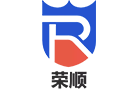快乐的童年
发布时间:2019-10-31 10:18:40
童年,对我来说是难忘的,也是快乐的。虽已阔别家乡三十多年,但每每回忆起那些往事,心潮起伏,思绪一下子回到那个梦幻的年代。
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,兄弟姐妹四个,父亲勤劳能干,母亲节俭持家。父亲时任生产队队长,每天准时带着社员出工,母亲虽然在管着家,但也要出工。那时的生产队是个大家庭,水田统一由队里管着,大家一起劳动,收获的粮食统一分配。队里天天开大锅饭,母亲等妇女成了煮饭工。当然只有白米饭,菜要自家带来。队员吃大锅饭时,有的蹲着,有的站着,干了半天活,肚子很饿,三下五除二,就把三大碗的饭吃个精光。生产队不煮晚饭,但下午四点钟会有点心发,这也是孩子们最盼望的事了。发放的点心有时是两个炸油包,有时是两个甜馒头,母亲总会留下一个,带回家给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分着吃。每年收秋后,生产队会杀一头大肥猪来庆祝丰收。全队男女老少,集中在晒谷场上,带上自家的桌椅,围摆成一桌一桌的。开席前,孩子们推着小板凳当汽车,互相追逐着,小嘴还不忘唱上《社会主义好》的歌曲。好吃的菜肴陆续端了上来,社员们争先恐后站起来夹菜,吃得津津有味,最好吃的,就数那道香喷喷的红烧猪肉了。
小时候的家乡,风景很优美,周围是郁郁葱葱的山林,一条宽阔的马路贯穿着整个村庄,还有一条清澈透明的小河环绕而过。山上有野猪、竹鼠等动物,稻田里有黄鳝、泥鳅,小河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鱼虾。父亲是捕猎能手,家里餐桌上就不缺荤食了。有一次,父亲的手腕还被竹鼠咬了,流了很多血,我们看了都很害怕。当我们长大一些后,会跟着大哥哥们夜间去叉泥鳅了。大哥哥们提着装满松树根的火盆,拿着泥鳅叉,走在弯弯曲曲的田埂上。清澈的水田里到处是泥鳅,哥哥们叉了一条又一条,自然是满载而归。水田里还有田鸡在呱呱叫,大哥哥们拿手电筒朝它一照,田鸡傻眼了,光顾睁着两只大眼,不会跑,乖乖就擒了。
冬季的早晨,父亲会带着年轻力壮的社员,挑上石灰头到泥鳅仑。然后往小河里撒下石灰头,过了一阵子,盼望的景象出现了,河里的鱼儿开始浮在水面翻白肚了,半生不死的,社员们急不可待跑下河里捞鱼,一会儿功夫,原先装石灰头的箩筐,现在装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鱼儿。太阳升起来,社员们挑着满箩筐的鱼儿也回到村里,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
家乡的山上长着一片片茂密的竹林,每年的冬季,社员们都爱上山挖冬笋。冬笋是大自然赐以人类不可多得的美味食品,质嫩味鲜,清脆爽口。冬笋还是一种高蛋白、低淀粉食品,它所含的多糖物质,还具有一定的抗癌作用。冬笋好吃却难挖,没经验的人一到竹林里就会满地乱刨,就像野猪来拱番薯地,甚至斩断竹根或连根拔起,这是犯了大忌,长辈们会指责的。我的父亲是挖冬笋的能手,他来到竹林里,先抬头望望竹枝竹叶的长势,他曾经教过我,长出墨绿色的竹叶往往是壮年竹,竹根上多半会长出几条笋。父亲选定了下手的目标后,再根据竹枝的朝向来判断竹根的所在位置,他用锄头轻轻地刨去表层的土壤,很快就看见金黄色的笋尖了。父亲一层一层地拨开笋前的泥土,一条粗大的冬笋露出来了,站在身旁的我,往往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,大声欢呼起来。父亲却很淡定,只见他麻利地抽出砍柴刀,架在在冬笋的茎部,用锄头一敲,完好的冬笋就取下来了。如法炮制,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四条,尽收囊中。往往个头不大的冬笋,父亲会手下留情,他总不忘把翻出来的泥土填回原处,并说这条竹根来年会长出春笋的。父亲用这种方法,挖了一条又 一条,不到半天,一个大麻袋装得满满的。父亲扛起重重的麻袋,我扛着锄头跟在后面,心满意足地回家了。冬笋会被修剪得整整齐齐,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,那些年的冬季,上山挖冬笋卖成为我们家最大的经济来源,真是靠山吃山呀!山林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,我们大家要爱护山林。
我们家的房子挨着生产队的仓库,父亲是生产队长,自然我们家就成了队里干部开会的场所。队里唯一的农村广播就装在我们家,那是父亲用来收听公社通知的工具。在那个没有娱乐的年代,因此给了我无限的欢乐。我喜欢那动听的歌曲,每天早上6点半广播准时播放,其中蒋大为、李谷一的歌声我尤其爱听。晚上9点半准时播放各种戏曲,最悦耳的是安微的黄梅戏,尽管不太明白曲中内容,但那如行云流水,委婉清新、细腻动人的唱腔,却令我仿佛身处其中,如痴如醉。我常常会因曲中情节的波澜起伏,内心难以平静,会因戏里人物的悲欢离合,久久不能入眠。在那艰苦的年代,美妙的歌声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,伴随着我健康成长,形式多样的戏曲文化,丰富了我内心的情感世界。我满怀对美好人生的憧憬,每天积极、向上地学习。
回忆往惜,再看今日,家乡湖坑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,崭新、独立的单元别墅拔地而起,整齐地排列在宽阔的村街两旁,高耸华丽的路灯,好似在站岗的英俊哨兵。到了夜里,亮堂堂的灯光,照亮了整个村庄,好一片灯火辉煌的美丽景象。目前,家乡正在挖掘红色历史根源,塑造闽西革命老区形象,如火如荼地建设美丽乡村。我魂牵梦绕的家乡,期待你的明天更美丽!
戴利荣
2016-11-18
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,兄弟姐妹四个,父亲勤劳能干,母亲节俭持家。父亲时任生产队队长,每天准时带着社员出工,母亲虽然在管着家,但也要出工。那时的生产队是个大家庭,水田统一由队里管着,大家一起劳动,收获的粮食统一分配。队里天天开大锅饭,母亲等妇女成了煮饭工。当然只有白米饭,菜要自家带来。队员吃大锅饭时,有的蹲着,有的站着,干了半天活,肚子很饿,三下五除二,就把三大碗的饭吃个精光。生产队不煮晚饭,但下午四点钟会有点心发,这也是孩子们最盼望的事了。发放的点心有时是两个炸油包,有时是两个甜馒头,母亲总会留下一个,带回家给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分着吃。每年收秋后,生产队会杀一头大肥猪来庆祝丰收。全队男女老少,集中在晒谷场上,带上自家的桌椅,围摆成一桌一桌的。开席前,孩子们推着小板凳当汽车,互相追逐着,小嘴还不忘唱上《社会主义好》的歌曲。好吃的菜肴陆续端了上来,社员们争先恐后站起来夹菜,吃得津津有味,最好吃的,就数那道香喷喷的红烧猪肉了。
小时候的家乡,风景很优美,周围是郁郁葱葱的山林,一条宽阔的马路贯穿着整个村庄,还有一条清澈透明的小河环绕而过。山上有野猪、竹鼠等动物,稻田里有黄鳝、泥鳅,小河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鱼虾。父亲是捕猎能手,家里餐桌上就不缺荤食了。有一次,父亲的手腕还被竹鼠咬了,流了很多血,我们看了都很害怕。当我们长大一些后,会跟着大哥哥们夜间去叉泥鳅了。大哥哥们提着装满松树根的火盆,拿着泥鳅叉,走在弯弯曲曲的田埂上。清澈的水田里到处是泥鳅,哥哥们叉了一条又一条,自然是满载而归。水田里还有田鸡在呱呱叫,大哥哥们拿手电筒朝它一照,田鸡傻眼了,光顾睁着两只大眼,不会跑,乖乖就擒了。
冬季的早晨,父亲会带着年轻力壮的社员,挑上石灰头到泥鳅仑。然后往小河里撒下石灰头,过了一阵子,盼望的景象出现了,河里的鱼儿开始浮在水面翻白肚了,半生不死的,社员们急不可待跑下河里捞鱼,一会儿功夫,原先装石灰头的箩筐,现在装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鱼儿。太阳升起来,社员们挑着满箩筐的鱼儿也回到村里,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
家乡的山上长着一片片茂密的竹林,每年的冬季,社员们都爱上山挖冬笋。冬笋是大自然赐以人类不可多得的美味食品,质嫩味鲜,清脆爽口。冬笋还是一种高蛋白、低淀粉食品,它所含的多糖物质,还具有一定的抗癌作用。冬笋好吃却难挖,没经验的人一到竹林里就会满地乱刨,就像野猪来拱番薯地,甚至斩断竹根或连根拔起,这是犯了大忌,长辈们会指责的。我的父亲是挖冬笋的能手,他来到竹林里,先抬头望望竹枝竹叶的长势,他曾经教过我,长出墨绿色的竹叶往往是壮年竹,竹根上多半会长出几条笋。父亲选定了下手的目标后,再根据竹枝的朝向来判断竹根的所在位置,他用锄头轻轻地刨去表层的土壤,很快就看见金黄色的笋尖了。父亲一层一层地拨开笋前的泥土,一条粗大的冬笋露出来了,站在身旁的我,往往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,大声欢呼起来。父亲却很淡定,只见他麻利地抽出砍柴刀,架在在冬笋的茎部,用锄头一敲,完好的冬笋就取下来了。如法炮制,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四条,尽收囊中。往往个头不大的冬笋,父亲会手下留情,他总不忘把翻出来的泥土填回原处,并说这条竹根来年会长出春笋的。父亲用这种方法,挖了一条又 一条,不到半天,一个大麻袋装得满满的。父亲扛起重重的麻袋,我扛着锄头跟在后面,心满意足地回家了。冬笋会被修剪得整整齐齐,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,那些年的冬季,上山挖冬笋卖成为我们家最大的经济来源,真是靠山吃山呀!山林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,我们大家要爱护山林。
我们家的房子挨着生产队的仓库,父亲是生产队长,自然我们家就成了队里干部开会的场所。队里唯一的农村广播就装在我们家,那是父亲用来收听公社通知的工具。在那个没有娱乐的年代,因此给了我无限的欢乐。我喜欢那动听的歌曲,每天早上6点半广播准时播放,其中蒋大为、李谷一的歌声我尤其爱听。晚上9点半准时播放各种戏曲,最悦耳的是安微的黄梅戏,尽管不太明白曲中内容,但那如行云流水,委婉清新、细腻动人的唱腔,却令我仿佛身处其中,如痴如醉。我常常会因曲中情节的波澜起伏,内心难以平静,会因戏里人物的悲欢离合,久久不能入眠。在那艰苦的年代,美妙的歌声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,伴随着我健康成长,形式多样的戏曲文化,丰富了我内心的情感世界。我满怀对美好人生的憧憬,每天积极、向上地学习。
回忆往惜,再看今日,家乡湖坑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,崭新、独立的单元别墅拔地而起,整齐地排列在宽阔的村街两旁,高耸华丽的路灯,好似在站岗的英俊哨兵。到了夜里,亮堂堂的灯光,照亮了整个村庄,好一片灯火辉煌的美丽景象。目前,家乡正在挖掘红色历史根源,塑造闽西革命老区形象,如火如荼地建设美丽乡村。我魂牵梦绕的家乡,期待你的明天更美丽!

戴利荣
2016-11-18
 在线留言
在线留言 地图导航
地图导航